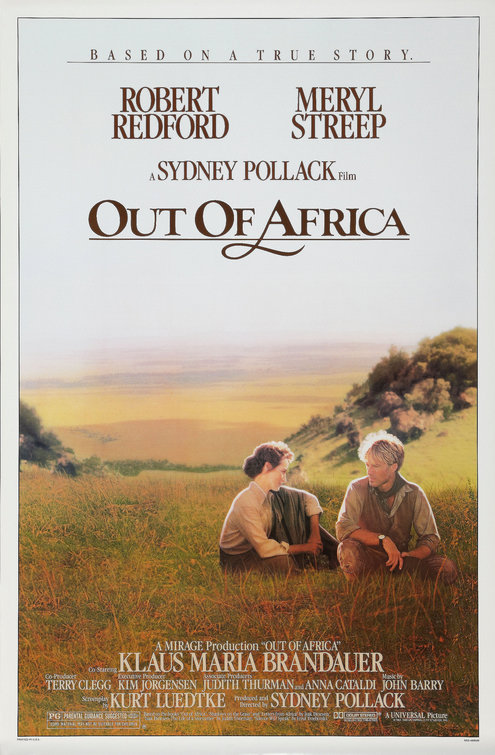本文发表在 rolia.net 枫下论坛“不对,”村长纠正道,“一个资产阶级的玩具,从城里来的。”
一阵冷意穿透了我的心,尽管屋子中央燃着熊熊的炉火。我听到村长又加了一句:“应该把它烧了!”这道命令立刻在人群中激起了一番明显的骚动。所有人都说起话来,吵吵嚷嚷的,你推我挤:每人都想夺过那“玩具”,亲手把它扔到火堆里。
“村长,这是一件乐器,”阿罗开口说话了,神态落落大方,“我的这个朋友可是一个优秀的音乐家,我说这话绝不是在开玩笑。”
村长又一把抓住小提琴,重新察看起它来。然后他把它递给我,那意思是让我拉一曲。
“对不起,村长,”我不无尴尬地说,“我拉得不太好。”
突然,我看到阿罗冲我眨了一眨眼睛。我心中很纳闷,便不由得拿起了提琴开始校音。“你们将听到莫扎特的一段奏鸣曲,村长。”阿罗说,跟刚才一样镇定自若。
我不禁大吃一惊,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,难道他疯了吗?好几年以来,莫扎特的所有作品,甚至任何一位西方音乐家的任何作品,都已经禁止在国内演奏了。在我进了水的鞋里,湿漉漉的双脚一下子变得冰冷冰冷。我又一次打起了寒战。
“奏鸣曲是啥子东西?”村长问我,语气中透着怀疑。
“我不晓得,”我开始结结巴巴地说,“一种西方的玩意儿。”
“一种歌吗?”
“就算是吧。”我支支吾吾地回答道。
当即,一种共产党员的警惕性重又闪亮在了村长的眼光中,他的嗓音变得充满了敌意:“它叫啥子,你的那首歌?”
“它很像是一首歌,但它是一首奏鸣曲。”
“我在问你它叫啥子名字!”村长嚷道,两眼直瞪瞪地盯着我。
又一次,他左眼中那三点红红的血斑令我害怕。
“《莫扎特……》”我犹豫道。“《莫扎特》还有啥子?”
“《莫扎特想念毛主席》。”阿罗又继续替我回答道。
好大的胆子!但是,它却十分有效:村长仿佛听到了什么神奇的指示,刚才还杀气腾腾的那张脸一下子就温和了下来。他的眼睛周围马上堆起了一层层的皱褶,露出了一丝幸福的微笑。
“莫扎特永远想念毛主席。”他说。
“是的,永远想念。”阿罗保证道。
当我紧着琴弓的马尾时,热烈的鼓掌声突然在我的身边响起,几乎让我有些害怕。我僵得麻木的手指头开始在琴弦上爬动,莫扎特的乐句返回到了我的脑海中,恰如忠诚可靠的朋友。农民们的脸,刚才还是那般的坚毅,在莫扎特清澈欢快的乐曲下变得一分钟更比一分钟温柔,仿佛久旱的禾苗逢上了及时的甘霖,然后,在煤油灯那摇曳不定的光亮下,渐渐地失去了它们的轮廓。
我演奏了好长时间,这期间,阿罗点燃了一根香烟,安安静静地抽着,听我拉琴,煞是一个成年人的样子。
这就是我下乡插队接受再教育的第一天。阿罗十八岁,我十七岁。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,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.net
一阵冷意穿透了我的心,尽管屋子中央燃着熊熊的炉火。我听到村长又加了一句:“应该把它烧了!”这道命令立刻在人群中激起了一番明显的骚动。所有人都说起话来,吵吵嚷嚷的,你推我挤:每人都想夺过那“玩具”,亲手把它扔到火堆里。
“村长,这是一件乐器,”阿罗开口说话了,神态落落大方,“我的这个朋友可是一个优秀的音乐家,我说这话绝不是在开玩笑。”
村长又一把抓住小提琴,重新察看起它来。然后他把它递给我,那意思是让我拉一曲。
“对不起,村长,”我不无尴尬地说,“我拉得不太好。”
突然,我看到阿罗冲我眨了一眨眼睛。我心中很纳闷,便不由得拿起了提琴开始校音。“你们将听到莫扎特的一段奏鸣曲,村长。”阿罗说,跟刚才一样镇定自若。
我不禁大吃一惊,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,难道他疯了吗?好几年以来,莫扎特的所有作品,甚至任何一位西方音乐家的任何作品,都已经禁止在国内演奏了。在我进了水的鞋里,湿漉漉的双脚一下子变得冰冷冰冷。我又一次打起了寒战。
“奏鸣曲是啥子东西?”村长问我,语气中透着怀疑。
“我不晓得,”我开始结结巴巴地说,“一种西方的玩意儿。”
“一种歌吗?”
“就算是吧。”我支支吾吾地回答道。
当即,一种共产党员的警惕性重又闪亮在了村长的眼光中,他的嗓音变得充满了敌意:“它叫啥子,你的那首歌?”
“它很像是一首歌,但它是一首奏鸣曲。”
“我在问你它叫啥子名字!”村长嚷道,两眼直瞪瞪地盯着我。
又一次,他左眼中那三点红红的血斑令我害怕。
“《莫扎特……》”我犹豫道。“《莫扎特》还有啥子?”
“《莫扎特想念毛主席》。”阿罗又继续替我回答道。
好大的胆子!但是,它却十分有效:村长仿佛听到了什么神奇的指示,刚才还杀气腾腾的那张脸一下子就温和了下来。他的眼睛周围马上堆起了一层层的皱褶,露出了一丝幸福的微笑。
“莫扎特永远想念毛主席。”他说。
“是的,永远想念。”阿罗保证道。
当我紧着琴弓的马尾时,热烈的鼓掌声突然在我的身边响起,几乎让我有些害怕。我僵得麻木的手指头开始在琴弦上爬动,莫扎特的乐句返回到了我的脑海中,恰如忠诚可靠的朋友。农民们的脸,刚才还是那般的坚毅,在莫扎特清澈欢快的乐曲下变得一分钟更比一分钟温柔,仿佛久旱的禾苗逢上了及时的甘霖,然后,在煤油灯那摇曳不定的光亮下,渐渐地失去了它们的轮廓。
我演奏了好长时间,这期间,阿罗点燃了一根香烟,安安静静地抽着,听我拉琴,煞是一个成年人的样子。
这就是我下乡插队接受再教育的第一天。阿罗十八岁,我十七岁。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,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.net